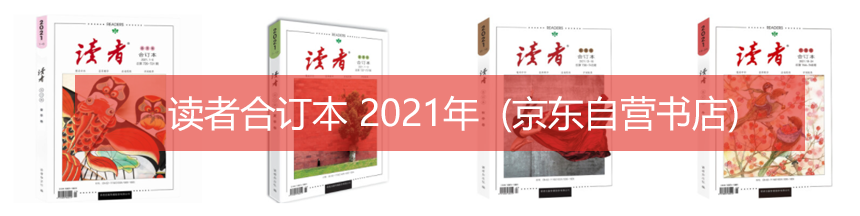基因的故事

我们都上了当
你见过黑人拉二胡吗?
呃……似乎难以想象。那你确定我们弹奏的那段布鲁斯、爵士乐就有把握能勾起黑人兄弟的乡愁?
在玩乐队的那些年,我时常会听到类似的对话和感慨。很多精于琴技的乐手,他们会去“攻打”布鲁斯、爵士乐。这固然是好的,那是西方现代音乐的根,更是摇滚乐的源头。有一次,我在深圳向一位朋友借了一批爵士乐磁带,他在眉飞色舞向我描述了音乐大师的厉害之后,把磁带交与我的同时,盯着我的眼睛怅然说道:“听一听,知道它们的好就行了,可千万别陷进去太深。”当时我是不解的,也是不服的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,这跟知识、勤奋之类的因素关系不太大。
我从电视上也看到过,一些外国人在武当山学习太极拳多年,打起来还是有些直胳膊直腿,全然不像中国人那般有绵中带韧的劲儿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上帝给我们的骨头中、血液里注入了什么?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看来这话真的很对。如果细说,我们自小听的水声、鸟叫,吃的饭菜的甜咸软硬,看到的雾色、月光,雨水的丰歉,还有我们脸上感受到季风吹来的方向,等等,这些无不是造就我们基因的点滴,也是造就我们的艺术和艺术品位的点滴。
十多年前,我还在做记者,有一次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采访。那次采访令我至今难忘,内容大概是关于南方发掘出的一座7000年前的古墓。考古单位在发掘古墓后,除了会把墓葬中的各种器物带走研究,通常会把墓主的骸骨交由人类学学者进行研究。那天,我是在中山大学的李法军博士的工作室采访,一到就见他正和学生用钩针、油画笔、镊子、小水枪清洗古人骨,清洗完再将人骨碎片用胶水拼合起来,最后通过分析,从中获得种种古人类信息。记得我和文字记者与李博士打招呼寒暄之后,李博士就盯着我的脸上下打量,不经意似的说:“我猜你是安徽人吧,蚌埠的?”“啊?太准了吧!”我着实惊异,因为我平时是个很不信“邪”的人。我脸上写着安徽还是蚌埠?他怎么看出来的呢?李博士却很坦然,说不是一定就能猜对,但总有个大概方向。我脸上肯定有信息,被他积累的数据给撞上了。那天下午,我很好奇地看着他工作,也问了很多问题。在说到我们的长相遗传、我们努力存钱留给下一代、我们在过年时玩了命往家赶之类的事时,正低着头进行“人骨拼图”的李博士淡然却又坚定地说:“基因!我们都上当了,我们都上了基因的当。”
那次之后,我开始很信基因。这个牵着我们往前走,渗透进我们的相貌、骨头里的“家伙”,不敢说是坏还是好,但我觉得认识它后,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就更透彻了。
谁是对手
前年,一位老太太从古巴来到广东台山祭祖。她叫何秋兰,并不是华人,而是生活在古巴的西班牙人的后裔,此前也未曾到过广东台山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?
故事是这样的:大约在1930年的古巴,西班牙裔女子何秋兰出生后刚满月,亲生父亲就去世了,她被当地一位叫方标的华侨收养。方标先生来自广东台山,一直教何秋兰讲台山话、学汉字。何秋兰4岁时就开始学唱粤剧,8岁登台,越唱越好、越来越红,人也越长越美。她常年在古巴有华人的地方演出,颇受当地华侨的喜爱和保护,这位貌美如花的白人姑娘成了千万里之外很有名气的粤剧传人。古巴革命后,剧团关闭,不能再唱戏了,何秋兰的生活变得十分潦倒。近年,摄影家刘博智先生于古巴发现了年华老去的何秋兰,披露了她的故事,并帮助这位洋血统喜欢唱粤剧的老太太回广东台山祭祖。
在一些热心人士的陪同下,何秋兰终于来到台山方氏墓地祭拜。令在场的人没有想到的是:何老太太突然在墓前着上戏装,唱将起来。唱腔如泣如诉,在场人士无不动容。
终于,这个时刻到来,她来到这个地点。这是一场没有血亲但饱含对抚育亲情和文化滋养的拜谢。这位外籍老人终于在这个地点,用曾经让自己安身立命的行头和语言宣示了自己的血统。
后来,我在网上看到何秋兰手抄的粤曲名段《星殒五羊城》唱本,唱词是中文,加了一些西班牙语的注音。唱本上写的是这样的词句:
真系雪样聪明花样命,
一朝魂断返蓬瀛。
空留得歌海芳名至今犹盛,
今日曲终人已杳,
唯余江上数峰青。
一个基因轮转的故事,竟然走了千万里,竟然用了一辈子。
我不知道何女士在成长过程中属于西班牙的基因留存有多少,但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到广东文化的浸染,活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因改造的特例。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自小在国外长大的“香蕉人”青年,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与西方人无异。这都说明,基因不是肤色、人种的事,而是人在出生以后被环境裹挟、浸染,经历各种你情愿或不情愿的人世流转后形成的。通俗地说,你在什么基因的酱缸里待过,你就会被染上什么味。搞艺术的人,作品里也会有自己的基因。就像那唱腔里、唱本上,满满都是。
在网上看到朋友转述这个故事后,我当时就伤心了。于是留言:“我们是基因的俘虏,而且也不是时间的对手。”
(湘 岸摘自兰州十月文艺出版社《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》一书,刘 璇图)
本站所有文章、数据、图片均来自互联网,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。
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。邮箱:dacesmiling@qq.com
严明 已更新 8 篇文章
分类排行
推荐阅读